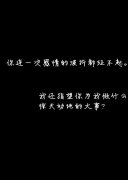从遥远的辽东本溪到美丽的江城武汉,从“山水甲天下”的桂林到“大雁东南飞”的衡阳,从繁荣的花都广州到边陲小镇桂南扶绥,我从军十余载,矢志报国、南征北战,心中总是萦绕着一抹浓郁的亲情,它激励着我在部队认真学习、刻苦训练、努力工作,使我从一名普通的社会青年成长为一名优秀士兵,从一名军校学员成长为一名优秀士官,从一名高中毕业生成长为已是本科学历,具有新闻写作、新闻摄影特长的“兵记者”……
十多年来,亲情是我自强不息的源泉,亲情催我去战斗。记忆中最深刻、最令我感动的是收到军营中第一封信、第一次探亲归队、上军校第一次给家中打电话时的情景,因为亲情,我把自己哭成一个泪人……
1994年12月底,我从湖南省邵阳县诸甲亭乡应征入伍,在辽宁本溪某部当兵。紧张艰苦的新兵生活压得我们这批“新兵蛋子”喘不过气来,但最揪心的却是入伍20多天竟无乡音。1995年1月12日中午,班长于化兵拿出一大堆信来,一一分发给我们。我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,颤抖地拆开书信,翻身上床认真读起来。信中,父亲嘱咐我继续发扬敢于吃苦、勤学好问的作风,努力在部队工作;弟弟鼓励我在部队干出个样来,为家争光。信中有一张淡黄色的纸引起了我的注意,上面的字歪歪扭扭,丑陋不堪,但一笔一画异常清晰。仔细一看,居然是母亲写给我的信。母亲可是只读过三个月书的“文盲”呀!我如获至宝,把这张信纸反反复复看了三遍。妹妹的手最巧,她把信折叠成一个千纸鹤,我只得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。妹妹说,自我参军后,母亲日夜思念,本来体弱多病的她又旧病复发,卧病在床。知道家中给我写信后,她艰难地爬起床,向弟弟口诉信的内容,又照着弟弟的字迹一笔一笔地抄写,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写成这不到两百字的信。妹妹一再要求我给妈妈写封平安信,让她安心养病。
读完妹妹的信,想着母亲硬撑着为我写信的情景,抚摸着母亲亲手为我写的信,我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,失声痛哭起来……
这是我在军营中收到的第一封信,也是母亲人生中的第一封信。
那担行李呀,承载着父亲一辈子的希望
母亲的信激励着我前进。在部队,我牢记母亲的嘱托,抢最脏最累的活干,处处冲锋在前,当兵第一年,我被上级评为优秀士兵;第二年,我光荣地加入党组织,并成为下一年军校培养苗子。1996年11月23日,阔别故乡两年整的我决定休假,探望远在南方的家人、亲友。考虑到家境贫困,我决定归队时带些土特产给部队首长战友,这样既经济又实惠,还最能表达心意。
我的倡议得到家人的大力支持,尤其是父亲,走乡串户为我张罗准备。勤俭节约惯了的他在购买土特产时特别大方。临归队时,我才发现里屋里已放满了茶油、猪肉丸子、腊肉、芋头等。
归队前一天晚上,父亲亲自下厨杀了一只大肥鸡为我饯行。全家人坐在火炉旁边吃边聊,很少喝酒的妹妹竟然喝了满满一大碗米酒。不知不觉已是凌晨一点,父亲催促我们上床休息,他和母亲为我准备行李。想着还有近3000公里路程,我只好提前休息。
躺在床上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屋里昏黄的灯光一直亮着,偶尔传来父亲清脆的咳嗽声。迷迷糊糊进入梦乡,一觉醒来,已是曙光初照,探头一看,父母正在为行李作最后的捆扎工作。原来,他们整夜没有休息,一直在为我准备行李。起床后,父亲交给我一根扁担,笑着说:“刚才和你妈称了有130多斤,只好用家中最好的扁担罗!”想想路途遥远,我面有难色,不知怎样把这笨重的东西带到东北;看着父亲憨厚的笑容,我又不忍心拒绝,父亲为我准备行李,走遍了附近十多个村庄……
我暗暗下定决心,就是死也要把行李带到东北。父亲坚持送我上火车。从乡下乘坐中巴车到邵东火车站后,他又忙着为我买车票,买水果,却命令我守在行李边别走动。火车还有10多分钟到车站,父亲突然想起我没有吃早餐,马上跑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面食店买米粉。
开往东北的火车终于进站,我抢着去挑行李,父亲怎么也不肯。我犟不过,只好双手托起扁担为父亲省力。父亲很吃力地把行李挑上火车,忽然发现刚买的米粉没带来,他二话没说,马上下了火车奔向候车室。隔着窗户,见父亲瘦弱的身躯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,心中无限感动。火车汽笛鸣响,父亲发疯似地冲出候车室,以最快的速度跨过栏杆,翻过月台,从窗户递给我尚有余温的炒粉。在我接过炒粉的一刹那,我发现父亲杂乱的头发竟然白了一大半,红红的眼圈掩饰不住整夜没有休息的疲倦。火车徐徐开动,父亲跟着火车慢慢的跑,一边挥手一边大声的喊:“挑不起就歇一会,到部队后马上打电话回家……”
扶了扶身边的行李,望着窗外在寒风中奔跑的父亲,我悲感交集,泪如泉涌……。
那一天,我在火车上哭了半个多小时……
心爱弟弟呀,兵哥哥欠你一辈子的情
回到部队后,我认真复习文化迎接军校招考。1997年7月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军械士官学校。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家人时,母亲在电话那头已哭得哽不成声。我以为全家在为我高兴,正想安慰家人一番,妹妹却接过电话,激动地说:“哥,你终于没让家里失望,你对得起弟弟了…………”
妹妹的话让我很蹊跷,我当兵两年多,年年被评为优秀士兵,当过班长,入了党,如今又考上军校,我怎么对不起弟弟了?在我的一再追问下,妹妹终于断断续续的告诉了我,当兵第一年弟弟打农药中毒晕死的事情……。
弟弟那年刚15岁。记忆中家中抬打谷机、打农药、车水等重活都由我这老大“承包”,弟弟象“跟屁虫”一样为我和父亲打打下手。我当兵一走,弟弟顺理成章的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。199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,毒辣辣的太阳把大地炙烤得象个火炉,四周无一丝风。而此时正是为稻田杀虫的最佳时机,弟弟毛遂自荐顶替我去打农药。
弟弟打农药没有经验。中午一点半时,刮起了南风,浓浓的农药味直往弟弟鼻子里钻,弟弟却不知道顺着风向打农药。由于天气闷热,农药中毒,弟弟渐渐觉得浑身乏力,他艰难地爬到田埂上,仰天一躺,准备休息一会再接着干。但一躺下就昏过去了。两点钟时,同村的建忠叔叔见弟弟大中午躺在田埂上晒太阳,怎么也叫不醒,跑近一看,只见弟弟脸色灰白,面无血色,双唇紧闭,急忙叫人把弟弟抬回家……
母亲扑在弟弟身上嚎声大哭,父亲一边采取掐人中、用盐搓身等方法抢救弟弟生命,一边差人拦车送医院急诊。正在邵阳打工的妹妹也急忙赶回,家中乱成一团。经过抢救,弟弟昏迷了三天三夜后,终于苏醒过来。知道事情的经过后,他艰难地爬起床说:“不要告诉哥哥,免得让他分神。”
弟弟打农药中毒昏迷三天三夜醒来后的第一句话,竟是请求大家隐瞒我,免得让我担心!我的心碎了,我的眼眶湿润了,我心爱的弟弟呀,兵哥哥欠你一辈子的情!在弟弟的一再要求下,全家人对此事向我闭口不谈,包括我上次探亲。
这一瞒,竟是两年。
电话那头妹妹也嘤嘤地哭起来了,我再也听不下去了,只能陪着妹妹泪流满面。为了支持我当兵,全家人不知为我作出多少奉献:弟弟因为那次中毒,体质大降,经常生病;妹妹才读完初中就辍学了;父亲坚持为弟弟治病疗伤,家中的农活一手揽;母亲省吃俭用,托着虚弱的病体日夜操劳,多次昏到在菜地上…
这一切,难道仅仅因为我是他们的儿子或哥哥?难道仅仅因为他(她)们是军属?
从此后,我对亲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,在紧张的工作之余,总隔三叉四地打个电话、写封家信回家,我仔细地记着每一位亲人一年中的每一个节日,尤其在他们的生日、父亲节、母亲节,我一定从遥远的军营寄一份礼物,打一个电话。亲情也无时不刻地激励着我在部队战斗,每当我捧着金灿灿的奖章、胸戴大红花登上领奖台时,我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心愿:亲情,你是我奋斗不息的源泉,我将用我的一生回报你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