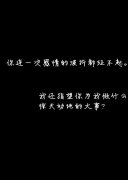七等生的短篇小说《余索式怪诞》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,正想好好看书,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,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。余索走到店里,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,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。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,只好落荒而逃,适于山间。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的佛乐,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,余索忍无可忍,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。
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,简直认同,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,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,有时甚于刀枪。噪音,是听觉的污染,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。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,并举歌德、康德、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,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。其实不独作家如此,一切需要思索,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,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。
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,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”,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“富贵病”。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,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“音源”抗议,或者向第三者,例如警察吧,去申冤投诉,一定无人理会。
“人家听得,你听不得?你的耳朵特别名贵?”是习见的反应。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,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,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,像余索一样,将不见容于街坊。诗人库伯(WilliamCowper)说得好:
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。
其实,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?《水浒传》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,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,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,一发狠,竟把垂杨连根拔起。
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,我们比他“进化”了这么多年,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。七等生的《余索式怪诞》刊于一九七五年,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十年以来,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。无论我怎么爱台湾,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,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。人声固然百无禁忌,狗声也是百家争鸣:狗主不仁,以左邻右舍为刍狗。至于机器的噪音,更是横行无阻。
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,商店用来播音乐,小贩用来沿街叫卖,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,寺庙用来诵经唱偈,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,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,扩大了杀伤的战果。四年前某夜,我在台北家中读书,忽闻异声大作,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,经过扩音器的“现代化”,声浪汹涌淹来,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,只凭其凄厉可怕,不觉其悲哀可怜。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,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,照例是没有结果。
噪音害人,有两个层次。人叫狗吠,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“原音”,无论怎么吵人,总还有个极限,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。但是用机器来吵人,管它是收音机、电视机、唱机、扩音器,或是工厂开工,电单车发动,却是以逸待劳、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,太残酷、太不公平了。
早在两百七十年前,散文家斯迪尔(RichardSteele)就说过:“要闭起耳朵,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,这件事我常感遗憾。”上帝第六天才造人,显已江郎才尽。我们不想看丑景,闭目便可,但要不听噪音,无论怎么掩耳、塞耳,都不清静。更有一点差异:光,像棋中之车,只能直走;声,却像棋中之炮,可以飞越障碍而来。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。台湾的人口密度太大,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。大家挤在牛角尖里,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,不,武器,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,认真取缔,未来的听觉污染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。
每次我回到台北,都相当地“近乡情怯”,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,怯于一上了计程车,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了我的耳根。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。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。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,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,或把音量调到极低,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选。
愈是进步的社会,愈是安静。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,不是落后,便是集权。曾有人说,一出国门,耳朵便放假。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,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省。